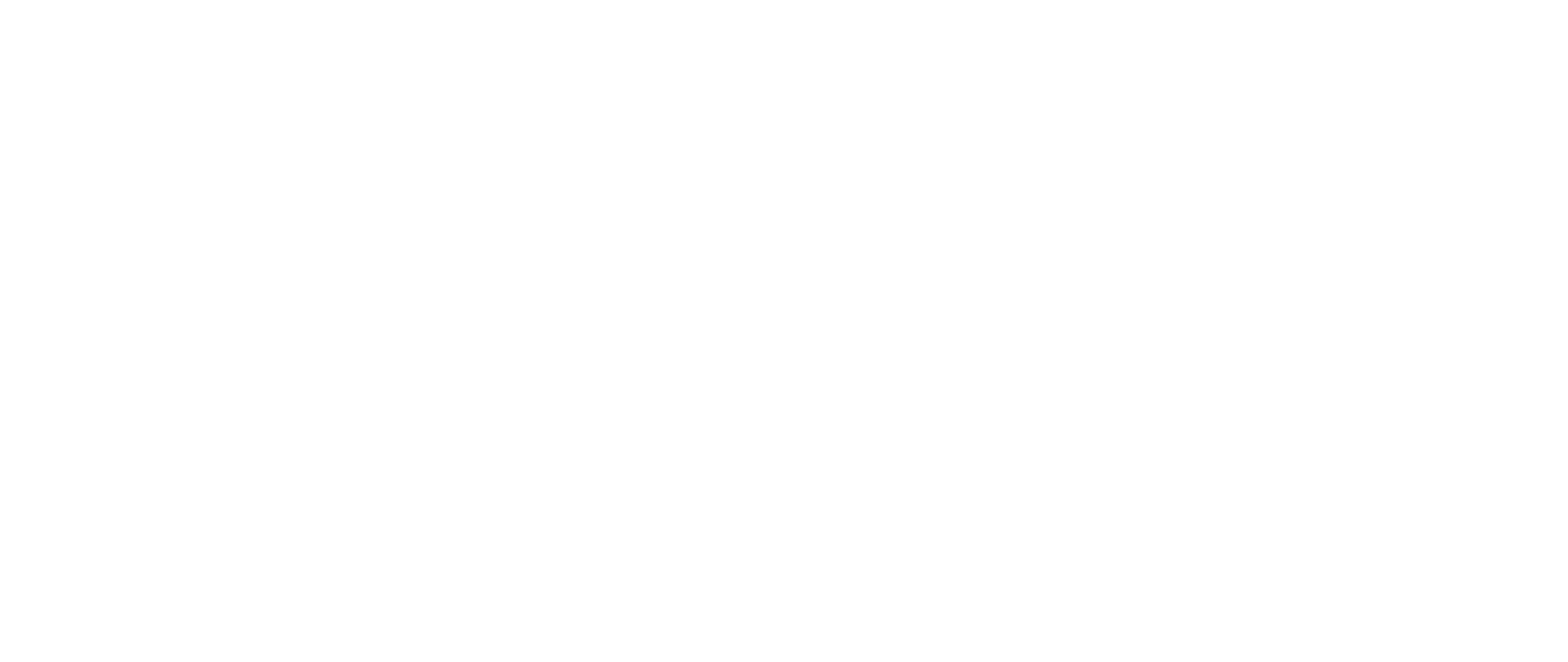導讀:我們對休眠的機制進行了綜述,並運用泌尿生殖系統模型對休眠原理如何應用於臨床進行了論證。數據顯示針對休眠的治療和診斷策略可以幫助醫師監控患者的休眠狀態
臨床轉化:生殖泌尿系統腫瘤
研究人員已對腫瘤的休眠機制進行了長期的探索研究,近年來治療策略的進展為將實驗室發現和新的理念付諸臨床試驗提供了契機。在臨床試驗中,缺乏有效的重現患者臨床前狀態的藥理學工具,成為此類轉化醫學所面對的主要挑戰。許多目前應用於腫瘤學的靶向藥物可能都涉及到了休眠的機制。在這裡,我們列舉了一系列關於生殖泌尿系統腫瘤的有說服力的範例,特別是以2005年索拉非尼(sorafenib)得到批准為標誌,這一領域前沿的免疫或抗血管生成藥物的研發進展。
基於Folkman 抗血管生成原理,新一代靶向VEGFR、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製劑藥物被批准用於臨床。例如,舒尼替尼(sunitinib),靶向抑制VEGFRs 和PDGFRs,於2006年被批准用於晚期腎細胞癌(RCC)治療;目前又有6款靶向血管生成的藥物被批准用於晚期RCC。一方面,這些藥物直接抑制血管生成因子,如VEGFR,它被認為與血管生成開關的“打開”有關,另一方面,這些藥物得到批准也是基於晚期、高收容量患者的試驗數據。關於血管生成休眠機理的更高關聯度的研究,應該在那些高複發風險、但目前無疾病證據的患者人群中展開。美國一項大型intergroup 試驗已經完成(數據尚未發表),對腎切除術後中至高危復發風險的腎癌患者行舒尼替尼VS索拉非尼(一種相關的酪氨酸激酶抑製劑)VS安慰劑治療的效果進行評估。這一輔助治療研究納入了若干臨床特徵不明顯、微轉移、高複發風險的患者,研究結果與休眠有關,因為後者決定了抗血管生成藥物延遲疾病復發的效應(表2)。
2010年,FDA批准新型免疫療法——自體細胞免疫治療——用於最低程度症狀、荷爾蒙治療抵抗的轉移性前列腺癌患者。這種療法使用了sipuleucel-T(一種晚期前列腺癌疫苗),它能夠召集患者體內的單核細胞,這種細胞由融合蛋白(PA2024)孵化激活,後者則攜帶著一種前列腺標誌物(即前列腺酸性磷酸酶)和GM-CSF。數天后,患者接受運載細胞再輸注,這導致了與對照組患者相比,sipuleucel-T治療患者的抗原特異性T細胞激動型指數增長了8倍,這個數據顯示了特異性T細胞對抗原呈遞的應答能力。從機制上來講,這一途徑與腫瘤免疫抑制直接相關且導致了休眠復甦過程中對抗原呈遞的抑制。雖然sipuleucel – T不會對傳統的化學療法和放射療法的相關作用因子產生明顯作用,但它會改善轉移性去勢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的總生存期。關於作用機理,有相當多的證據支持將這一療法應用於微轉移灶治療或輔助治療,因為這一療法可預防因T細胞功能被抑製而導致免疫監視功能失去,並且可延長腫瘤休眠期。 sipuleucel- T臨床應用於早期或轉移性患者是目前腫瘤臨床研究的熱點。研究者還評估了自體免疫細胞治療應用於切除術後高複發風險膀胱癌患者的輔助治療的效應。
節拍化療與抗血管生成療法的聯合應用
節拍化療(metronomic chemotherapy)策略的出現比以上描述的方案都要早,還有一些對於前列腺癌治療途徑的早期評估也促進了與休眠理論相關的臨床治療途徑的討論。節拍療法需要頻繁地給予化學藥物治療,與之相對的是最大耐受劑量化學療法,它的給藥次數較少。節拍療法中,一些細胞毒素化療藥物可以使腫瘤保持在休眠狀態,同時所造成的不良反應較少,當與抗血管生成療法聯合使用時特別有效。其中一項早期研究報導了標準激素治療抵抗的晚期前列腺癌患者使用環磷酰胺和地塞米松進行節拍化療。值得注意的是,在8個月的中位應答持續期內,68%的患者前列腺特異性抗原(PSA)的血液水平下降超過50%(標準PSA應答),隨後的前列腺癌研究也發現了相似的結果。然而,由於這一領域缺乏大型隨機試驗的數據,因此阻止了這一途徑作為標準的癌症治療策略的應用。
除上述臨床效應外,節拍化療或可對維持腫瘤休眠產生更直接的作用。 Pietras 和Hanahan等人報導了抗血管生成藥物聯合節拍化療的體內研究。利用胰腺神經內分泌瘤轉基因小鼠模型,他們發現PDGFR抑制減少了脈管系統的周細胞包裹指數(Pericyte coverage index),這使得上皮細胞對化療更加敏感。如果高劑量的環磷酰胺可誘導顯著但短暫的腫瘤應答,那麼PDGFR抑製劑與節拍環磷酰胺的聯合使用就可誘導出更長期的腫瘤消退反應,這種效應可能是通過關閉血管生成開關產生的。
對於轉移性原發腫瘤的手術切除效應值得期待,這種效應可能與腫瘤休眠相關。對RCC,前酪氨酸激酶抑製劑靶向治療時代的兩項隨機研究顯示減瘤性腎切除術(cytoreductive nephrectomy)可使已知轉移疾病患者產生生存期獲益。雖然這些臨床背景可能並不會與腫瘤休眠有直接關聯,但這些發現顯示原發腫瘤與疾病的遠期結局間可能有相互聯繫,研究人員在一些稀有病例中觀察到,RCC行減瘤性腎切除術後自發性轉移現象消退,這一結果支持上述觀點。然而,一些臨床前的研究顯示,原發腫瘤可能會控制轉移灶腫瘤的生長,在這些模型中,摘除原發腫瘤會促進遠端腫瘤的生長,這些現象強調,需要進行特異性的臨床研究以明確手術治療與休眠間的關聯。
結論
現在的證據提示腫瘤休眠機制並非獨立存在,相反它經常依賴於一些常見的信號通路,這些信號調控DTCs生長使疾病發展為臨床可檢測到的轉移。對腫瘤休眠的研究仍然處於嬰儿期,一些發現相互矛盾,需要謹慎解釋。隨著一些獨立研究小組的研究獲得進展,某些爭議也會迎刃而解。屆時,關於這一領域的三個方面——細胞休眠、血管生成和免疫潛伏——均會出現強有力的證據,證明其與腫瘤休眠的調控相關。此外,這些機制似乎具有一些共性,這使得對三個方面的分層更加困難,勿庸置疑的是,所有三個方面的機制均有偉大的臨床意義。在不久的將來,腫瘤休眠領域將有望產生多項的新概念、新發現。未來的挑戰在於我們能否開發出基於腫瘤休眠機理的治療策略。未來將會誕生更精確、非侵入式、經濟可靠且長效的腫瘤休眠監測技術,以支持上述治療策略的應用。隨著我們對腫瘤休眠領域理解的深入,臨床醫師將會獲得更多的診斷和治療方案,以防止致命的癌症轉移復發。
關鍵字:#休眠腫瘤靶向治療的臨床機